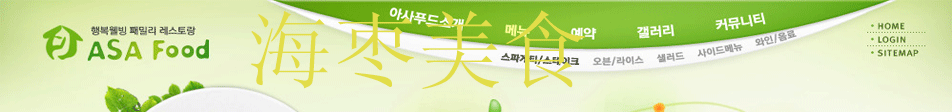|
门牌号是标识,也是一种符号,小小门牌号的后面也会有很多神秘有趣的故事。 作者:薛原 南海路7号 南海路7号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临海的“生物楼”二楼海洋地质室房间,留下了我的青春记忆——我在那儿工作了15年。现在的生物楼,与20年前相比,早已装扮一新,记忆中生物楼的走廊里总是暗淡拥挤,贴墙排列的资料柜陈旧斑驳,像是蒙着历史的灰尘。只有五层的“生物楼”是大院里的主楼,年冬天我刚参加工作来到房间时,赵老师自豪地说,别小看了生物楼,你看看墙有多厚,当初盖大楼时可以盖高些,地基打的很结实,为什么不盖高呢——为了防备战争,我们海洋所建在海边,打起仗来容易遭到炮火,这样厚实的墙就是炮轰也不容易轰塌。更让我开眼界的是到职工澡堂洗澡,老师带着我去,说我们的澡堂是防原子弹的。原来职工澡堂建在地下室,沿着楼梯往下走,心里直打怵,灯光昏暗,水气弥漫,一间间地下室,一个个大水池,像是一间间水牢。老师说,你猜得不错,“文革”时这里就是关押人的牢房。 与生物楼比邻的是“水族楼”,里面有一个“人工海洋”,是我们招待从外地来的师友的保留节目,当初来了外单位的同行,往往先领着他们参观位于生物楼一楼的标本陈列室,然后就是人工海洋。每次带人参观,就要到生物楼三楼的标本室去找马先生,马先生一辈子的精力都给了海洋生物标本,从马先生那儿拿到钥匙,老先生总是再三叮咛,标本怕晒,看完了标本一定别忘了拉上窗帘关好灯锁好门。在“生物楼”里当时还有许多老先生,大多是从事海洋生物分类学的,几乎一位老先生就是一门“学科”。 说起海洋所的老先生,几乎就是大半部新中国的海洋科学史,譬如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毛汉礼、刘瑞玉、齐钟彦……与海洋生物学相比,我们地质室所属的学科年青许多,老先生只有一位张兆瑾先生,是清华大学上世纪30年代初的毕业生,瘦小的老先生还是清华大学校友会的副主席,据说老先生的拉丁文非常了得,但在我的印象里,老先生几乎不参与具体的课题项目了,我们地质室当时的几位权威还只是副研究员,也就是副教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譬如秦蕴珊、赵一阳、金翔龙和陈丽蓉等人。十多年后秦蕴珊和金翔龙当选了院士,不过金翔龙早已调到了杭州。那时微机还是稀罕物,秦先生让我在稿纸上写了几行字让他看看,说写的不错。于是,我就开始为他们抄写文稿了。当时的“副研”已很难得,每个月还发额外的花生油票和鸡蛋票。不象现在,博导和研究员满大院都是了。 那些年外地来了朋友,在海洋所的小饭店吃过了晚饭,往往领着他们在海水浴场的沙滩上漫步,说这是我们招待朋友的“大客厅”,然后再漫步到八大关,说这是我们的“后花园”。说这话时,谁能想到后来我会离开这儿呢。 鱼山路36号·童第周故居 老山东大学对于青岛来说,是挂在嘴上永远的骄傲和遗憾,与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等文科教授相比,童第周先生是理科名家的代表。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以童先生为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后来发展成规模为全国海洋科研机构第一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作为海洋研究所的创建者,童先生担任所长一职的时间从50年代直到70年代“文革”结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实,童先生当时除了担任海洋研究所所长,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还在科学院京区的动物研究所兼任着职务,并已移家定居北京,对青岛的海洋所更多是“遥控”领导,他真正在青岛的生活还是在老山大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鱼山路36号老山大宿舍挂上童先生的故居铭牌顺理成章。 童先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海洋生物学家,他是一位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家,如果查阅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海洋科学卷》,不难发现,中国海洋科学家条目里并没有收入童先生的大名,“童第周”条目出现在大百科全书的《生物学卷》里。海洋研究所的生物学研究在当年主要是海洋植物和海洋动物(又分海洋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分类学,在这些“显学”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发育生物学,这就是童先生的“嫡系”学科了。童先生于青岛的意义,更多的是一个象征,一种从历史的昨天走到今天的科学与文化的传承的象征,就像童先生的科研工作从早年直到晚年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那是是属于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的一个很专门的领域。 童先生的一则轶事印象难忘:童先生早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时,和他住在一栋公寓里的一位舞文弄墨的诗人在餐桌上以傲慢的口吻嘲笑了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的愚昧。童先生愤怒了,对这位诗人说,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我们来比一比,看看是我们中国人聪明还是你们这些洋人聪明。童先生要和诗人比试的是文学写作。后来在女房东的劝说下,那位诗人向童先生道了歉,童先生也收回了要放弃生物学改行文学的宣战,仍回到了实验室里。对这则轶事,除了童先生强烈地民族自尊心外,更令人感叹地是,假如当年童先生一怒之下改行从事了文学创作,还会有童第周与我们这座“海洋科学城”的不解之缘吗。 莱阳路28号·张玺故居 张玺先生与青岛有“缘”,早在年春天,他就来到了青岛,在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的资助下,张玺和他的助手开始了第一次青岛胶州湾海洋动物调查,这也是我国学者组织的第一次海洋动物综合性考察,对于学科建设有着开拓性意义。 年夏天,作为原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所长的张玺先生带领着原班人马来到了青岛,与从老山东大学出来的童第周、曾呈奎一起,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莱阳路28号就是当初的几处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之一。 张玺先生来青岛工作并非他的本意,是服从新中国成立后科研部门统一布局和建设的需要,张先生的夫人和子女都没有来青岛,他是孤身一人率领着老部下们来青岛创业的。但来到青岛后,他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对于新中国的海洋科学事业,张玺先生的贡献为人称道的是走出学术象牙塔的实用的贝类学,他的《贝类学纲要》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贝类动物学的专著,他还组织领导了我国海洋无脊椎动物的调查,全面查清了我国海域蕴藏的无脊椎动物资源。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历数张玺先生的学术贡献已显得多余,倒是有一件张先生的轶事值得我们思索——张玺先生是年赴法国留学的,那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碰撞着各种各样的思潮,那是一群有着格外敏感的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在里昂的咖啡馆里,张玺曾听过周恩来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是带着好奇心来听这些年轻共产党人的演讲的。在纷繁多样的主张中,张玺没有走革命的道路,而是决心踏踏实实地学到一门学问,像张玺这样的选择,在当时,被称为科学救国派。不过,在后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张玺先生解剖自己的思想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他在法国留学时因为自己是“公费生”,便感受不到“勤工俭学”同学的艰难,也就缺少对“革命”的向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大多选择了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张玺先生于年7月10日在青岛去世。他的弟子说,要是没有“文革”,以张先生的性格该是个活大岁数的人。 福山路36号·毛汉礼故居 作为一名物理海洋学家,毛汉礼恐怕难为一般读者了解,除了在百花苑文化名人雕塑园内矗立的一座毛先生的青铜雕像,现在再在福山路36号挂上毛汉礼故居的铭牌,也许是毛先生在海洋科学界之外亮相于我们这座城市的寥寥无几的一个“机遇”了。百花苑内的毛汉礼雕像表现的是毛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时的形象,一身西装的毛汉礼显得风华正茂。其实,晚年的毛先生,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譬如,80年代初,身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的毛先生,与新中国建国后50年代培养的那一代学者相比,在日常工作中,一个习惯上的小区别就是,毛先生批阅文件或留言致书往往都是握一管秃笔,写一手流利的毛笔字,这也是毛先生那一代老学者的特点,中西结合,文理兼通。有一张80年代初期海洋研究所几位主要领导的合影,也能反映毛先生晚年的传统色彩,大家都是西服领带,惟有毛先生是典型中式的对襟襻扣罩褂。 “物理海洋科学”距离我们过于遥远,倒是毛汉礼先生当年从海外归来的轶事更能激发我们的想象。抗战胜利后,毛汉礼赴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任职于美国的著名海洋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毛先生回国的努力遭遇到美国政府的阻挠,直到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毛先生的归来才得以实现——周总理签字用朝鲜战场上被我们 抓获的美军战俘作为交换,才使得毛先生能够启程回国。从这则轶事也能看出,新中国的领袖们对科学家的重视和渴求。 毛先生的学术贡献毋须多谈,像毛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对于新中国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开宗立派,奠定一门学科的成长,“中国物理海洋学”与毛汉礼的名字密不可分。中国的海洋科学,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全国海洋普查”是一件摸清我国沿海“家底”和奠基学科大厦的“战役”,毛先生就是这场“战役”的一位主要指挥员。如果说海洋普查是“务实”,学术著述是“务虚”,那么毛先生归国后编著的《海洋科学》,则对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有“开山”的作用。 福山路36号是海洋研究所的一幢老宿舍楼,毛先生在这里住了很多年,“文革”后毛先生又搬到了也处于福山路上的新建的另一幢宿舍楼上,若说“故居”,自然还是36号的老楼老屋。对于这片宿舍楼来说,挂上毛汉礼故居的铭牌其意义并不在于“名人效应”,而是对于我们这座城市来说,人文精神的张扬和文化底蕴的建设不仅仅在于如“老舍故居”、“粱实秋故居”、“沈从文故居”等等文学大师的“遗迹”保存,“当代”的海洋科学及其已走入历史的学科“掌门人”,其人其事其“影”,也已融入城市的文化传统中,“海洋科学”所蕴涵的城市文化更是我们青岛这座“海洋科学城”的精神财富。 齐河路5号·“古巴楼” 齐河路5号这栋风格独特的小楼为何叫“古巴楼”,其实我并不知道。这栋小楼是海洋研究所的宿舍楼,据说当年是为了给苏联专家修建的,建筑风格是体现的古巴国的建筑特色,因此被称为“古巴楼”。但楼盖好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也就变成了宿舍楼。当然,住到这栋楼里的绝非等闲之辈,例如,这栋小楼里住着曾呈奎,曾先生是海洋所创办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海带之父”;这栋楼里还住着齐钟彦先生,齐先生是张玺先生的传人,在他的努力下实现了张先生未竟的念想——成立了中国贝类学会,齐先生是首任中国贝类学会的会长,是一位在贝类学研究上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着的老学者……这栋楼里还曾住过当年的海洋所的党委书记孙自平,一位一直到年代仍被海洋所的许多老师们怀念的老干部,孙书记的革命资历很老,在海洋所的科技工作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文革”中含冤自杀了。 对我来说,这栋小楼还有着特殊的“亲切”,因为这栋楼上还住着秦蕴珊陈丽蓉夫妇,正因为这对夫妻科学家,我才对这栋小楼有特殊的印象,因为我年冬进入中科院海洋所时,被分配到海洋地质研究室,而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就是秦先生(秦先生担任海洋所副所长,研究室主任是兼任)。当时我们海洋地质室,在海洋所属于老先生稀有的“年青研究室”,资历“老”的,主要是几位“副研”:秦蕴珊、赵一阳、陈丽蓉等。他们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海洋地质科学家。记得有一次我们研究室的支部书记让我给秦先生送一封信,说送到秦所长家。我问秦所长家住在哪里?支部书记说,你沿着南海路到黄海饭店,再走到齐河路就看到古巴楼了。当时,黄海饭店是新建起的“地标”性建筑,但是我不知道啥是“古巴楼”。支部书记感叹我不知道“古巴楼”,说海洋所的人还有不知道古巴楼的?!我确实不知道,也由此对这栋楼有了一种神秘的认识。 这栋小楼,当年住着两位中科院的院士,这就是曾呈奎和秦蕴珊。边上不远邻近百花苑,曾是中科院青岛休养所的院落,现在,那个院落里盖起了一栋体量虽然不大但看上去很端庄的“院士楼”,海洋所的院士们都住进了这栋崭新的院士楼。与院士楼相比,历经风雨的“古巴楼”显得落寞了许多,但却依然是一道别致的老风景。 薛原:本名薛胜吉,年出生于青岛,《青岛日报》副刊编辑。著有《闲话文人》《画家物语》《海上日记》《检讨:旧档案里的中国海洋科学权威》《南海路7号》和长篇小说《蓝桅杆》等,编有《独立书店,你好!》系列和《如此书房》系列等。 时光印记体验券中奖名单 每人一张 张菱**** 丁女士**** 张文婷**** 孙静**** 赵成**** 闵爽**** 张槿颜**** 宋继荣**** 贾明圆**** 朱湘**** 杨娴婷**** 周云凤**** 昌莉2**** 张印**** 张彩霞**** 王雅楠**** 张海燕**** 徐国庆**** 朱琦源**** 王秋雯**** 领奖时间地点 领奖时间:年12月27日至29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逾期视为弃权哒) 领奖地点: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号市南软件园5号楼1层青岛新闻网前台 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