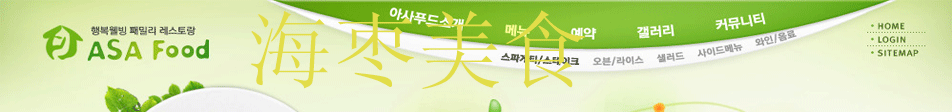|
白癜风好治么 http://m.39.net/pf/a_4791291.html 出土铭文青铜器说明,己与?是商周时期不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国家。由于文献记载的阙如,已与?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以往研究多存争议。烟台上夼己器与?器同出一墓后,已与?是否为一个国家又成为热议。作者先前也因上夼己器与?器同出一墓,赞同一国说。近年在对烟台出土铭文青铜器的整理和思考过程中,认为问题并非如此。一是在考古发现中,不同国别的铜器同出一墓的现象常见,不能简单地将国别不同的铜器视为一国。二是上夼墓中已器的“华父”与?器的“叟”,未必有着必然的联系,同为一人。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烟台地区出土的已器与?器作一梳理,并就上夼墓出土的己器与?器的国别及?国的地望、“纪侯大去国”后之地望等与之相关的问题作些探索。 已与?国别考证略说 对铭文青铜器中的己国即文献记载中的纪国,其国都在今山东寿光境内的认识,学界基本无疑。而对不见于文献却在铭文青铜器中有较多发现的?国,与已国是一个国家,还是属于两个国家,历来学界的观点截然不同,可分为一国说和二国说。(一)己与?为一国说最早提出已与?为一国的是清代学者方濬益先生。他对宋代以来引用汉人卫宏说证明?国与杞国同之说表示怀疑,提出为姜姓,杞为姒姓,两者不是一国;并进一步指出,?国即姜姓纪国。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国录考释》中同意其观点,认为杞乃姒姓之国,?与杞非一也,谓?亦纪。曾毅公、陈梦家、杨树达诸先生亦从此说。李白凤先生在《东夷杂考》中也赞同郭沫若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清季出土于寿光纪侯台下之纪侯钟,乃书作“己”,是称“?”,省作“己”,春秋以后称“纪”。烟台上夼已器与?器同出一墓后,又成为己与?为一国说的新证。齐文涛在《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认为己华父鼎的华父与?侯鼎的弟叟应是一人,叟乃其名。李步青先生在上夼墓清理简报中认为,上夼?国铜器和已国铜器同出一墓,应系一人之器,即墓主名叟号华父,证明?、己本系一国之称。李学勤先生在《试论山东新出土青铜器的意义》中认为,原报道上夼墓器主系一人是正确的,己?互见,是?在金文里纪的又一写法,而不是另一姜姓国。张博泉先生在《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中认为,上夼墓的?侯是已侯的又一写法,即纪侯。李沣先生在《探寻寿光古国》中则认为,上夼墓的已和?为一国的不同称谓。高广仁、邵望平先生在《海岱文化与齐鲁明》中赞同上夼?器和已器的器主当为同一个人的看法,是纪国公室贵族无疑,已、?并用或通用。林仙庭先生在《扑朔迷离看己国》中亦从李步青先生之说,认为上夼墓的器主名叟号华父,叟与华父是一个人。这两个人名之前的国名?与已也应是一国之名的不同写法,?国与已国就是一个国家。近年来,许多地方史研究者也多从此说。(二)己与?为二国说否认已与为一国说的有容庚先生。他在评价《山东金文集存》时说,?侯恐非纪侯,对纪、?为一国说表示怀疑。王献唐先生在《黄县?器》中认为,已器与?器在时间和字体上的不同,可证明已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杜在忠先生在《寿光纪器新发现及几个纪史问题再认识》中,依据年寿光新出土已国铜器及以往有关资料,也否认纪、?为一国说。崔乐泉在《纪国铜器及相关问题》中认为,纪和?当为商周时期两个不同的姜姓小国。孙敬明先生在《甲骨金文所见山东古国与商王朝关系》中认为,纪、?均为姜姓,但渊源有各,商代纪、?,一在山东寿光,一在河南淇水流域,终非一国。高明英先生在《商周?国研究》中也认为?非纪,?与纪是两个国家。除上述已、?国别两说外,还有?、杞为一国说;?、蓟为一国说;?为箕子朝鲜说;已、齐为一国说;纪、莱为一国说;纪、?、莱为一国说等,可谓众说纷纭。因诸说已超本文所论,故对诸说论点不再述及。上夼?器之巽非纪国辨析 持上夼墓出土已器与?器为一国说的论据,主要有两点:一是两器同出一墓;二是推测?侯弟叟鼎的“叟”与已华父鼎的“华父”同为一人。已器与?器同出一墓,是否能作为已与?为一国之说的证据,是值得商榷的。考古发现说明,不同国别的青铜器同出一墓是常见的现象,原因同国与国之间的联姻、赠送、赏赐、赗赙或战争等因素有关。因而上夼已器与?器同出一墓,不能作为己与?为一国的证据。相反,上夼己器与?器同出一墓,正是己与?不同国属的有力证据。?侯鼎(现藏于烟台博物馆) 纪国与?国是商周时期两个势力较强的国家,同为姜姓。尽管有分析两国有着共同的族源关系,但均在商代立国无疑。年,在寿光北右城遗址出土一批商代晚期青铜器,19件铸有铭文。其中2件铭“己”、1件铭“己甲”、15件铭“己并”,证实纪国至迟于商代晚期在寿光一带建国。在晚商帝乙、帝辛卜辞中,有“?”、“?侯”之称,又可证?国至迟也在商代晚期建国。出土和传世已器与?器说明,从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已器与?器同时并存,年代未有中断。进入春秋时期,仅见?器出土,未见已器出土。这些发现说明,已与?应是不同国家的名称。若为一个国家,其国名在同时代的金文中,字体虽有变化,但一般不会出现不同的用字。至于为何出现已与?是金文的又一写法的认识,可能与?字从己,与己有关。在这方面,王献唐先生在《黄县?器》中对已非杞亦非?作过详论,不再赘述。“叟”与“华父”为同一人,最早是齐文涛先生在《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叟”系器主之名,华父与叟应是一人。其后,李步青先生在原报道中认为,两器同出一墓,应系一人之器,即墓主名叟号华父。吴洪涛、林仙庭先生考释叟与华父皆有老者之义,从李先生之说。李学勤先生则将叟释为“弁”。虽然弁与华父字义不同,但也认为原报道作器者系一人,华父是字,是正确的。由此看来,推断叟与华父为同一人,并非完全依二者字义确定的。按着推理,如果两器的形制、年代相同,铭文的国名用字相同,虽然器主名用字不同但字义相近,推断为同一人有着较大的可能性。同理,如果两器主名用字相同,而国名用字不同,虽可以说二者是同一国名的异写,但也存在着不确定性。问题是上夼两器的国名用字不同,器主名用字也不同,因而叟与华父、己与?就很难说为一人和一国之关系。?侯鼎铭文 归城、上夼与异国地望 ?国建于商代,亡于春秋。其地望众说不一。按现行政区划分,大概可归为河南、山西、北京、辽宁和山东说。在诸说中,有的因时代不同,其地望也发生变化。为体现学者观点的完整性,现以学者考定的商代?国地望归类,并对持周代?国地望变迁的一同述之。河南说:主要有张俊成先生的安阳一带;朱活先生的?本在王畿之内,周灭商后迁到燕都东北;孙敬明先生的商代在河南淇水流域,周初迁辽宁大凌河流域,西周中期大凌河流域?族的强支迁山东半岛即墨一带。山西说:主要有李学勤先生的山西箕城;曹定云先生的殷初在今山西浦县“晋人败狄于箕”之处,殷代为北方燕地,春秋为山东莒县北部;陈槃先生的?之初国本在山西,渐迁河南,最后迁山东。北京说:主要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的殷商青铜器》报告的周初的燕地,今北京沙河一带;彭邦炯先生的北京附近;何景成先生的燕地?侯;高明英先生的商代中晚期至周初在北京一带,西周中期迫于戎狄的压力南迁山东,西周晚期及春秋定于山东黄县归城一带。辽宁说:主要有阎海先生的在祖先发源的故地,与孤竹等一起成为商朝在北方的方国。山东说:主要有王献唐、逄振镐、何光岳等先生的莒县北境;李白凤先生的最初以黄县为中心,殷时因受殷的侵略,一部分迁到辽东半岛,河南安阳、洛阳的?器是?降附商后内迁的产物;王永波先生的商代在临朐一带,西周时期因受齐国的迫胁,逐步向半岛深处移动,远达黄县、烟台等地;还有王恩田、齐文涛先生的周代在山东东部和烟台一带。从以上学者考证研究的结果来看,除李白凤先生认为?族最初以黄县为中心外,商代?国的地望几乎与烟台地区无涉。进入周代,龙口归城南埠村和烟台上夼?国铭文青铜器的发现,将人们的视线引向龙口和烟台。?国无论是由北迁入,还是从西进入,多认为与龙口、烟台及所处的胶东半岛有关。对周代地望考定较为具体明确的有高明英先生的黄县归城一带,齐文涛先生的烟台一带,孙敬明先生的即墨一带,王献唐先生的莒县北境。其论据,前两者多侧重?器出土地的推定,后两者则多结合地名的推断。这里仅就龙口归城和烟台上夼涉及与?国地望相关的问题作些分析。归城,又名灰城,是胶东地区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周代古城址,有内外两城。内城建在河边台地上,城墙内外设有环壕,面积22.5万平米。城内已探明17处大小不等的夯土基址,最大的面积为平方米,应为宫殿基址。外城沿内城四周的山丘顶部,依势构筑,面积约8平方公里。其建筑规模与鲁国故城相当,为都城性质无疑,年代为不晚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历年来,多次出土重要铭文青铜器。除上述两处己器、?器地点外,还有年归城小刘庄出土了3件铭文青铜器,其中启卣、启尊两器记述的大致为一事,是启随昭王南征之事,年代为西周早期。关于归城的国属,学界虽有分歧,但多认为是莱国都城。其论者,多依年石良镇鲁家沟出土的莱伯鼎为据。年石良镇集前赵家出土的里(莱)父鼎又为其说增添新的物证。就目前材料而言,虽然不能统一归城为莱国都城的认识,但更无法证实归城是国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南迁或东移之地。一是归城的年代与?国南迁或东移的年代不合。以归城小庄、归城M1及与归城领主相关的石良镇庄头墓群、鲁家沟墓群、集前赵家墓群出土的铭文青铜器年代来看,归城的年代至晚应在西周中期的早段。二是归城古城址的规模与?国被迫南迁或东移时的国力不符。归城如此规模宏大的内外城墙、环壕及大型宫殿基址的形成,不但需要有在这一地区强大的统治势力,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一个南迁或东移国家的国力是无法办到的。三是西周早中期归城领主与?国同周王朝的关系不同。归城小刘庄、鲁家沟等地出土的多件青铜器铭文显示,归城领主在西周早中期就与周王朝关系密切,曾多次参与周王朝的东征、南伐等重大军事活动。而?国未见西周早中期与周王朝关系的铭文记载,所见只是西周晚期参与周王朝征淮夷及与周王宣联姻的铭文记述。四是归城领主与?国是联姻关系。虽然集前赵家出土西周中期的?器,但因铭文残损不能确定其性质。归城南埠村出土的器,铭文明确是?国君主为其女儿出嫁陪送之器,可证归城领主与?国是联姻关系。以上四点足以说明,归城非?国都城,与?国是联姻关系。同样,归城也不是纪国大去其国后的新都。归城出土的西周晚期已侯鬲为媵器,又证实归城领主与纪国也是联姻关系。因而,归城应是与莱国关联最大的故城址。上夼所在的芝罘区,春秋时称“转附”,是先秦时期的著名港口,又是齐地八神中的阳主之地。史载齐景公欲观于转附,秦皇汉武多次幸临祭祀阳主。考古发现证实,这里曾是先秦时期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域中心。这一地域中心,虽早被现代城市化的高楼大厦所湮没,但上夼和烟台二中纪国与?国铭文青铜器的出土,为解开这一地域中心的历史面纱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上夼墓出土的已器与?器,上文已辨析已与?不是一个国家。这样,芝罘上夼一带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纪国的领地,另一种可能是?国的领地。有学者认为是纪国的领地,有学者认为是?国的领地。作者赞同上夼一带为?国领地的看法。一是上夼墓?侯弟叟鼎的出土,是?国在上夼一带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在无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是考证研究该地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烟台上夼和龙口归城、集前赵家所出?器,是山东地区唯一有清楚出土地点的?国器物,在明确归城非?国都城后,上夼?器就成为判断?国地望在上夼一带的重要实物证据。二是从铭文的内容来看,上夼?侯弟叟鼎是直接与?国君主相关的器物。而已华父鼎虽然是纪国的华父所作器物,但存在着是否与纪国君主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烟台二中出土的己爵为西周中期,不能作为纪国在春秋早期大去其国地望的物证。这也是赞同上夼一带为?国领地非纪国领地的因素之一。已华父鼎与己爵显示的应是纪国与?国两国之间关系的实物证据。已爵又为上夼一带古国地域中心可能形成于西周中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齐地八神在胶东地区的四神中,阴主、月主、日主三神与所在的曲城、归城、不夜城古国地域中心,形成的年代均不晚于西周中期,为确定阳主所在的上夼一带古国地域中心可能形成于西周中期提供了佐证。三是若?国在西周中期由北京一带或辽宁大凌河流域南迁至山东半岛之说成立的话,迁入上夼一带的可能性要大于迁到即墨一带。一是上夼出土有与?国君主相关的铭文青铜器,而即墨一带虽有?山、不其得名或许与?国有关,但却未出土与?国相关的实物证据。二是从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上夼位于半岛的北部,?国南迁到岸后即可到达。而即墨位于半岛的南部,?国南迁到岸后需长途跋涉穿越半岛的腹地才能到达,远不如上夼一带便利。总之,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国的地望在上夼一带的可能性最大。前河前与纪侯去国后之地望 《左传·庄公四年》(公元前年)载:“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文献中的纪国历史自此中断,究竟去向何方,也是众说不一。旧说有清康熙十一年和道光七年《沂水县志》记,距县西北的纪王崮,相传是纪侯去国居地;高士其引《城冢记》说,邹县东南有纪城及纪侯冢,相传为纪侯去国避难处。此两旧说现已被考古发现所否定。年,纪王崮发掘了春秋时期贵族大墓。从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器物的特征来看,应属莒文化范畴。邹县的纪城,又名纪王城,实为春秋邾国故城。新说除何光岳先生的纪人南迁至江苏贛榆纪鄣城一带外,几乎均认为在山东半岛的烟台地区,只是具体地望不同。王献唐先生认为,纪国那时只有一条路可走,向东边远处走,通过莱国迁到东莱为止;王恩田先生认为其新都有可能就在黄县归城;孙敬明先生认为纪国向东莱迁徒地点应在上夼一带;常兴照、程磊先生认为纪国的鄣邑应该就是前河前遗址,并为纪侯大去其国的流亡方向找到踪影;《山东省历史文化遗址调查与研究报告》认为,前河前为己国遗址与墓葬区;持已与?为一国说的学者,则多认为上夼一带和前河前一带都是纪国的活动范围。由此看来,对纪侯去国地望的具体位置还需要作些分析。一是纪侯大去其国向东迁移的方向,为胶东半岛的烟台地区是可以肯定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流亡之国,显然不可能还有如此强大的实力,统治着烟台上夼和莱阳前河前一带的两个古代地域中心。在上文中已论述龙口归城与纪侯去国地望无涉,烟台上夼一带为?国地望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推断莱阳前河前遗址为纪侯大去其国后之地望,则有着更多的合理性。莱阳位于胶东地区的中部,是古代半岛与内陆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也是现代国道由淄博、潍坊经平度、莱西,东达半岛最东端的文登、荣成的重要交通枢纽,又远离齐国故都临淄,因而可能成为纪国东迁的选择之地。考古发现又说明,前河前遗址也是一处周代古国或邑城的地域中心。即有纪国的贵族墓群,又是面积很大的居住遗址,还可能存在城址。前河前墓葬中出土的已侯壶为纪国君主作器,是判断纪侯去国地望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若如有学者考证纪国的鄣邑是前河前遗址不误的话,更可证前河前遗址为纪侯去国后之地望。二是鄣邑应与纪侯去国后的地望相关联。《春秋》庄公三十年(公元前年)载:“秋七月,齐人障。”《公羊传》《谷梁传》皆说鄣为纪之遗邑。此载可知,纪侯去国26年后,齐国才把纪国降附。因而,鄣邑是最有可能成为纪侯去国后的居地。关于鄣邑之地望,杜预在《左传》注解中说,在东平无盐鄣城。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却说,在海州赣榆县之北七十五有纪鄣城,亦曰纪城。王献唐先生在《山东古代的姜姓统治集团》中,则详细论述了这两地距齐、纪均甚远。如在东平或赣榆,当时中隔鲁、莒、向、邾等国,纪国无法统治,齐人的势力也远不到这些地方而收降纪邑,降之也无法统治。进而推定鄣之地望仍在纪国外郑、晋、部各地一带。常兴照、程磊先生从前河前遗址具有城邑性质、“纪人代夷”地理位置、五龙河古代俗称漳河等三个方面的分析,认定纪之鄣邑应该是前河前遗址。作者认为,王献唐先生论之有理,赞同纪之鄣邑不在东平或赣榆之说。常兴照、程磊先生的鄣邑就是前河前遗址之说,虽是一家之言,但论据较为客观,与前河前遗址的文化内涵和遗址的年代相吻合。前河前遗址为纪之鄣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通过以上的分析,作者提出了上夼?器之?非纪国之己,上夼一带为?国之地望;归城非纪亦非?,为莱国之都城;前河前遗址可能为纪之鄣邑,是纪侯去国后之居地的初步认识。当然,随着今后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工作的深入,上述认识可能得到验证或更正,这正是作者所期待的。(完)编者按:作者王锡平系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文中图片由研究会会员赵家增提供。 往期精彩回顾 芝罘讲述(12)——葡萄山周边的的老洋房烟台海坝工程建造始末《图说烟台老洋房》一书面世发行阴主祠探微从筑城到城建:开埠后烟台城市空间的嬗变开埠后烟台城市人口的演变历史上的烟潍铁路始末(下)历史上的烟潍铁路始末(上)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简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