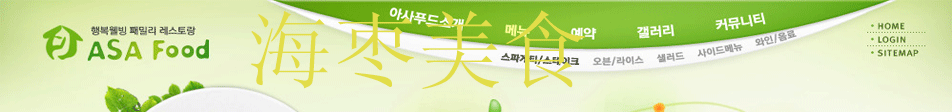|
莱阳聚焦:莱绢的回忆 文/原德庆 几年前,曾制作了十几个美篇,写了些关于莱绢过去的工作生活小碎片,今天就以她们为蓝本,再梳理成稿,重温在莱绢三十多年的美好回忆。 初识莱绢 一九八零年我十八岁。十二月五日,我们一行几个人坐着部队大院的解放卡车一起到了莱阳县城。当时到绢纺厂报到的人最多,有五个人,三男两女,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我是第一次到绢纺厂,也是第一次到莱阳县城。 我们农村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世面,临走时娘叮嘱我说要老实,不惹事,好好做事,一定要有出息云云。 报到是在绢纺厂东宿舍里。接待我们的是管理室负责人单定一师傅,高高瘦瘦的,大家都叫他“大老单”。他给我们逐一登记后,引我们把铺盖行李放在宿舍管理室隔壁的小平房里,告诉我们这个月的十号再来上班。 {年轻时的宿舍管理员“大老单”(单定一与妻子苏慧真)} 东宿舍当时只有两三座宿舍楼,两三层。在靠近火车站通往汽车站的路边立着,除此之外,都是清一色的红墙红瓦的平房,分别为甲排、乙排、丙排。乙排的前面对着东宿舍西门的地方,威严地立着毛主席慈祥的画像,画像的两边,有“抓革命,促生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之类时代色彩很浓的宣传口号。 出了东宿舍西大门,沿斜对面的丁字路口往西走差不多二百米,就到绢纺厂大门口了。大门朝南,对面是绢纺厂大礼堂,很气派地矗立着。在大门口附近转转,印象最深的是厂区输送暖气的管道冒出来的热气,烟雾缭绕,仙境一般。 当时正值午饭的时候,不时有人从云雾中穿行,大冷的天大都穿着单衣,要么身上披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上面沾着白棉花(当时以为是棉花,其实叫绢纺花毛)。穿梭的人群中,手持的饭盒里,诱人的饭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莱绢就这样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了。 融入莱绢 在家里的时候,就听说莱绢是省属国营企业,部队分管我们这帮小青年就业的负责人说,上莱绢要考试,所以我们都铆足劲复习课程。我的学习成绩还行,在到莱阳以前我刚考上村里学校的民办老师,因为招工户口能出来,我毅然决然的离开学校。 我们这批新工人有二百七十多人,是莱绢历年录取工人最多的一批。 人太多住宿不好安排,男的都住在礼堂西侧的一排小平房,女的全部住在礼堂门头房的二楼,这都是刚腾出来的房子。床都是铁制的,上下铺,一个宿舍装下三四十人。女工的宿舍我不知道,男工宿舍门的挂锁,可真是一道风景,一个门上四五把锁,多的时候六七把,环环相扣。可这样也锁不住,有时候有人钥匙丢了,进不来就把门给撬开了,所以门不闭户是常态,经常是这样的情况,晚上你不在这里住,床是闲不住的……厂里有摄影爱好者,曾经把门上挂连环锁的照片投了省内的一家报刊发表了,照片的题目好像是《禁锢》,意为呼唤改革的春风,我觉得是一片精悍的力作,引人深思且发人深省。 (年在宿舍门口留影,背后小楼即传说中的“小红楼”,当年的莱绢招待所和服务公司) 我原以为进厂分配工作之前是要考试的,按考试成绩分配,结果没有考试,直接宣布分配,我被分配到制绵车间当了切绵工人。因为当时保全维修工、电工什么的是羡慕的工作,本想通过考试能争取一下,希望没了,心里挺难受的。 工作劳动很快就化解了心里的疙瘩,和工友们慢慢地熟了起来,交流也多起来,不再觉得孤单。从他们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什么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快乐和幸福。火热的劳动生活,让我融入莱绢这个大家庭;平日近人的老师傅,让我感觉到这个家的温暖。 我的师傅 徐秀英是我的师傅,她是一个特别好的人。那时我们和师傅的关系都是特别的亲近,就像现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绝对听从师傅的教导,毕恭毕敬的虔诚,所以我们进步也快,没有多久就可以单独挡车了。由于技术不精,卷绵时经常出现大肚子绵,大小头绵,要么就是绵子拉地不紧,出了松棒绵,这时候师傅就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们,言传身教做到了极致,师傅这种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 刚进厂时我时常想家,师傅了解后,就与我进行交流,并邀请我到她家里玩,甚至作客,这给我很多的安慰。在师傅的关怀帮助下,我不仅享受到了家的温暖与快乐,更加安心地工作,踏实地做事。一次,徐师傅一家人要回老家,师傅的爱人祁师傅把家里的钥匙递给我说:“晚上没事的时候就来看电视吧,顺便也给我们看看家。”我满满的感动,眼睛是潮湿的,只为了那份沉甸甸的信任。 (年轻时的徐秀英师傅) 年轻的经历是充实的,记忆是深刻的,时间过去多少年过去了,闭上眼睛也能喊出好多师傅工友的名字——徐秀英、宋其香、王克强、祁天成,还有郭庆龄、衣龙凤、接庆友、刘晓美等等。 融入生活 后来厂子慢慢地为我们改善了住房条件,从大宿舍搬出来,住在了三个人一间的小宿舍,开始过上了“小日子”。后来我在莱绢恋爱、结婚、生子,莱绢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记得刚进厂时,我们的月工资是二十四块钱,再加上中夜班费差不多有三十块。我一个月攒五块钱的储蓄,一年下来就买了块烟台“北极星”手表,那时习惯动作是扬起来手看时间,其实是在炫一下自己的手表。 出徒时工资好像是三十四五块钱。那时的钱结实,一个月十块钱的菜票可以吃香、喝辣的。不过我们也不太舍得,一个馒头票再加五分钱的馅饼,那馅饼又香又好看,使劲咬一口,留在嘴里会有几小块五花肉;一个馒头票加两角菜票,就可以吃到莱绢食堂四个肉光光的小包子了,那时出力多、也长身体,饭量好,吃六个小包子正好,可又舍不得,所以只吃四个包子再加半个票的馒头,就几瓣生蒜,吃的那个舒坦呢!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时不时地想起莱绢的馅饼和小包子。 俗话说:“轻工业不轻,重工业不重”,指的是上班时间和劳动强度。四年三班倒的车间生活是那样的难忘,辛苦,更有快乐!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的,一天的工作不觉就过去了,大家在累身上,快乐在心里。 绢纺工人的工作,其实是一种美丽的重复。就说我们一等切绵工吧,落丝工把开茧球平整均匀地铺在切绵机导入绵板上,在导入辊的咬合下均匀在喂入,滚筒上的七排钢针除杂梳理并缠绕在滚筒上,定速定量地喂入。切绵机的偏心轮转完指定的齿数,自动划开皮带轮,此时操作工一手握紧剪刀,轻轻地抓紧皮带轮,右脚踩住制动踏板,滚筒刚停稳,迅即掀开滚筒防护盖,右手挥动剪刀顺着剪刀槽,按照一定的角度剪开割断滚筒缠绕的丝绵,然后把剪刀放在操作台上,双手抓起七根圆圆小棍,压在水盒里含满水的丝绵中迅速地擦动几下,踩住制动踏,把剪开的丝绵缠绕在水湿的小棍上,然后放在绵板上排放整齐,再迅速盖上滚筒防护盖,几乎同时拉动皮带轮归位闸,一气呵成,新一轮的切绵过程又开始了。 多少年过去,切绵的活早就不做了,但过去的一切,已铭刻在骨子里,像烙印一样。这印在心里的东西,是无法忘记的。 (年参加读书演讲比赛) 记得在厂里读书演讲的时候,我是这样描述我的工作: “我用挥舞的剪刀裁出最美的丝绸图画,沾水盒里荡漾的是春天里一池春水,起伏错落的小棍是直抒心意浪漫的指挥棒……亲爱的朋友啊,又有谁不说我们绢纺工人的工作是最美的心灵的歌唱呢……”几十年过去了回响在大礼堂上空的激情澎湃依然冲撞着我不老的心胸。 岁月留痕 我的班组是制绵丙班,在车间的四年时间里,工长换了几茬,工人来来去去的调换,或者调走,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丙班。 我对丙班有着特殊的感情。第一任工长叫梁德堂,穿上工作服的梁工长,看上去是一个标准的北方农民。平日里他最常见的工作服是灰色或者蓝色的,就连帽子也是这个色调,模糊地记得都是中山服,扣子总有几个没系好,不是不系,压根儿就是扣子丢了,他却懒得去缝补上,灰帽子或者蓝色的帽子的盖,扭着向上面翻着S波浪型。梁工长一米六出头的粗矮身材,一口黄牙,大概是抽旱烟留下的。梁工长的笑是甜润而喜庆的,但印象最深的是他发火时急转直下,瞪圆的大眼睛,急露露的,眼珠子要蹦出来的架势,工作上他要求你不能含糊,完不成任务,偷工减料它会吵的你抬不起头来,你干得好他就露出满口黄牙朝你笑。他对我们生活摸得准,谁家有困难他就帮你解决,是个热心肠的人。梁工长是我在丙班担任工长时间挺长的一个,后来他调到基建科,带着一个徒弟在厂内干油漆活儿。他负责任,不讲情面,我们心里服他。后来知道他的家是农村的,老婆孩子都在农村,礼拜天骑着车子要回家,春播秋收,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这样想来,混看他都是个农民也就不奇怪了。 杨金海、徐少强、林则刚三位师傅都在丙班担任过工段长,我和徐少强相处的时间最长。后来我调任原成会计,他是原料库的班长,接触就更多了,彼此之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车间里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很多,工作上总是鼓励我放手去做,这对我来说都是难得的锻炼,这些是无法忘记的。徐少强师傅比我要大六七岁,也早退休了,上次回莱阳搬家遇到他,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提着蔬菜瓜果之类的,岁月的痕迹无一例外的镌刻在他的脸上,街头偶遇让我们惊喜,握住彼此的手,说着聊着,忘不了的兄弟情义,说不完的知心话。 (80年代初参加绢纺专业培训) 这样想着,我的眼前蓦地浮现出徐慧师傅的影子,她是我们厂的劳动模范。个子不高,但舍得出力,工作范围的事她做的好,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她总是抢着去做,来的早、走的晚,经常在上班的时候,远远的看到她在厂里忙碌的身影。关于她的事迹,我并不能详实地都说出来,但人们都服她,这是事实,做的多,说的少,所有人都对这样勤快的老实人过不去。 其实细细想想,在我们莱绢这样平凡的人真的太多了,你不能因为她(他)不曾被评为先进,就是做的不好,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是我们莱绢人骄傲的品格,正是他们一个个站立着,才顶起了莱绢这片天空。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工人下岗,但我们莱绢的工人,在再就业的队伍里,却是有目共睹的佼佼者,因为她(他)们是莱绢人,她们身上融入了莱绢的精神,她(他)们在各行各业延续着莱绢人的良好形象与精神。 礼堂轶事 职工大礼堂是我们莱绢人的骄傲。当时莱阳的企业只有莱绢、莱拖、莱动有大礼堂,平时开会、演节目,放电影什么的大型活动都在礼堂里。 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看电影是最好的业余享受,莱绢有自己的礼堂和专职电影放映员,几乎是每个周末都能看上一场电影。每逢周末孩子们是最快乐的,早早吃了晚饭,闹嚷嚷地在礼堂外面的操场上跑来跑去,礼堂门一开,就像一群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跑进去抢座位。 那时候,有电视的人家很少。平日里大家要么去看电影,要么像挤破头似的跑到礼堂边上的电视室里看电视。印象中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武松》、《加里森敢死队》、《卡桑德拉大桥》,还有日本的电影《追捕》、风卷全国的电影《少林寺》……屋里人满了,那时年轻不怕挤也不怕站,不看到电视说“再见”不休息,回到宿舍后还要再感慨、议论一番,下半夜才会渐渐平静下来。 八十年代初是拨乱反正的时期,莱绢排演了几部大型话剧。我那时担任剧务跟着一起跑前跑后,所以记得清楚些。印象最深的是话剧《命运》,周林坦师傅是导演也是主演之一。我记着赵家骅、杨海云、葛青、鞠家福、范丽珍、郝建祝、尹汉平、孙星华、徐兴信等个个表演精到。 (作者(后排左二)在话剧《命运》中担任剧务) 《命运》就是在礼堂排演的,有时白天上班下班排练,晚上排练更是家常便饭,大家都付出了许多,但都不曾有丝毫的怨言。演出非常成功,后来都轰动了莱阳,辗转部队、机关演出多场,为莱绢争得了荣誉。 关于大礼堂的记忆绝不仅仅这些。八十年代初,莱绢团委举办读书演讲比赛,我参加了而且得了好成绩。至今还记得比赛那天,会场黑压压的,到处人头攒动……这也激发了自己的情绪,登上讲台我似乎忘记了一切,面对他(她)们我用心在呼唤—— “朋友,你见过搏击长空的雄鹰了吗?你看它呼啸着振动着钢铁的翅膀,勇敢的冲向了黑色的风暴……朋友,这是一幅多么雄壮的画面啊!你也许会想,如果有一天,我也有这么一双钢铁的翅膀有多么好啊!朋友只要你读书,认真的读书,知识一定会给你安上钢铁的翅膀……”,这是我演讲的开头,接下来我滔滔不绝,一气呵成,顺利完成了演讲,我成功了! 也正是因为这次表现,我引起了厂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