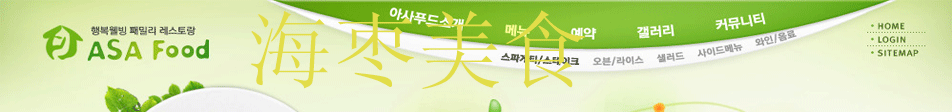|
来源:学海编舟记编辑:学长 金耀基:父亲自幼受儒学熏陶,文采斐然,载誉乡里 我出生于浙江天台。父亲金瑞林自幼受儒学熏陶,文采斐然,载誉乡里。虽然因为祖父早逝,家境贫寒,但所幸祖母贤德有识,为了培养父亲,变卖祖田,助他读书识字,以走出天台县岭跟山区。父亲很争气,少年的时候在家乡就声名远播,县太爷问他一句诗,他马上就能答出下一句来。我母亲的家也在天台,不过她的家境比较好,但也没有培养出学者。 父亲虽然读的是现代的东西——法律,但因为那个时代,所以四书五经也还是要读的。我想,他们那个年代比我们其实更困难,新东西要学,旧东西还没有放弃,我们成长的时候旧东西基本上都逐渐放弃了,除非你主动去看四书五经,但其实很少有人会再去念四书五经了。我父亲出去以后,因为有意仕途,就念法律,他念得很好,加之国学根底好,很快就平步青云,20多岁就开始做民国政府的县长,先是东阳县县长,后是海盐县县长,算是不错的。那时候的县长几乎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在离任东阳县县长时,上千县民夹道相送不舍,故后来有回任东阳县之美事。因为做事方式受到大家的推崇,我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祖母去世时,她的棺木经过几个县城,所到之处都大开城门,礼遇过境。 抗战时期,父亲去了重庆,日本人打到浙江了,我们就在家乡跟着母亲逃难。从杭州,往南逃到磐安县冷水镇,再往南最后逃到丽水那边的景宁县。景宁地处山区,当时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我记得逃难的时候,母亲用一根扁担挑着我和弟弟两人,我坐这头的篓子里,弟弟金树基坐那头的篓子里,就是这样逃的,所以这段历史我常因心痛而不太去讲。逃到一个地方住下来,听说日本人又要来了,接着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的小学根本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谈不上完整的读书,都是断断续续的。 抗战胜利以后,父亲也回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是吴国桢,宣铁吾将军任警察局局长兼沪淞警备司令部司令,听说父亲文笔好,同时正派、清廉,就邀请他出任上海警察局秘书长。那个时候官场盛行“五子登科”,因为汉奸很多,光复以后如果接收大员喜欢什么人的房子,打个电话就可以拿来了。但是,父亲从来就没干过这种事情。除了国民政府配给他一栋洋房——那是日本人占据时候的一个处长的房子,一辆林肯牌的美国汽车,此外就是两袖清风。他不肯外出应酬,也没有外快,连父亲的司机老刘,在跟他做了半年之后也因度日拮据,最后哭着要求调离。 父亲政声好。年国民党第一次行宪,召开国民大会,他决心返乡竞选国大代表,与他竞争的是国民党天台县党部主任。其间波诡云谲,远非父亲最初的设想。所幸终因乡民奔走相助,连许多老婆婆都不惧山区跋涉之苦,去县城投了父亲一票。这些老婆婆未必懂什么民主,但她们知道父亲是好人、清官。不过,即使父亲胜选,还有过差点被取消当选人资格的闹剧。 父亲在上海落脚后,我们也从老家搬来和父亲团聚,住在静安寺附近,我也在那里上中学,所以到现在我也还会说上海话,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吧。不过,没有几年,国民党就失败了。尽管父亲因包括竞选在内的个人遭遇对国民党自然有他自己的感受,但年他考虑来考虑去,最终还是决定随国民党撤往台湾。我们家走的时候,论关系没问题,他是上海警察局的秘书长;但是要有钱买船票或机票呀,我父亲哪里有钱?正好国民政府配给了我们一栋房子,可以卖了换成钱嘛!但其实父亲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真的走,因为他觉得走太麻烦了,等于整个把根都拔掉了。我到现在也不敢讲完全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总之是一拖再拖,拖得相当后,而在这个拖的过程中,有时候房价一天跌一半——就这样跌的,所以最后就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别人。 杨中芳:父亲带我们去台湾 年底,爸爸托人去买船票到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家除了妈妈爸爸,已有三个小孩,我是老二。我妈妈原先哭死哭活不想去台湾,可是没办法,我爸爸说一定要走,全家都要走。他一声令下,我妈哭是哭,但还是跟着去打预防针了。我们三个孩子是跟着妈妈,还有一个帮忙的亲戚,由天津坐船去台湾的。那时我爸已经飞到上海,去结束他的生意,后来经香港和我们在台北会合。就这样,我们一家人莫名其妙地“逃”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先被接待暂住台北山东会馆,那时候我3岁多吧,没有印象,这都是听我爸说的。我爸好像从大陆带了一两根金条,就用这些钱跟他朋友到台中开了一家龙口粉丝工厂,结果听说全赔光。回到台北,他想想还是回去做他熟悉的老本行吧,就在台北重新做起染料进出口生意。 到台湾不久,我就和姐姐一起上小学了,为了让妈妈能专心照顾妹妹。所以我比人家念书早很多,我跟黄光国同年,他在台大却比我低两级。我上的小学叫“国语实验小学”。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大家讲“国语”(普通话),因为当地人原来都是讲闽南语的,于是就成立一个小学,叫“国语实验小学”。刚进去念书时,我记得每次考试我都是零蛋,因为年纪太小,大概只有4岁。每天坐在那里,不知所学,老师一叫我起来,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老师就说:“杨中芳,你为什么这么爱哭?我一叫你站起来,你就哭。”我到现在还记得她说话时的厌烦样子。当时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怎么这么爱哭。现在当然理解了,人的智力是要到一定年龄才发展起来嘛!当时成绩单上的数字都是红的,因为都不及格,后来才慢慢赶上。 叶启政:祖孙三代反映了台湾的历史变迁 在历史上,很少像我或比我更年长之一代的台湾人一样,祖孙三代刚好成长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的祖父生于清朝统治时期,而于日据时期过世;父亲生于日据时期的大正时代,并历经国民党统治;我虽生于日据时期,但两年后就在国民党统治下成长。说来,台湾人数百年来的命运,就是在不断改朝换代的文化夹缝中走向未来。 我的祖先来自福建同安辖下的一个小村庄,至于是哪个村庄,来台之后我是第几代,我自己都说不上来。我的祖父出身地主阶级的士绅家庭,原本准备参加科举以求功名,但还来不及应考,在他13岁时,台湾就被日本强占了。面对新来的陌生占据者,除了做个悠闲“吃租”的地主士绅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发挥的空间。祖父虽选择当“顺民”,但他与新竹地区文人成立诗社,吟诗填词,搜集古玩,还曾参加报社举办的诗作比赛,得到全台冠军的头衔。他读的都是中国传统的书籍,如郑板桥的诗集、《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小说《花月痕》。这一切显得,新来的日本占领者,似乎与他的实际生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日本文化更走不进他的世界,他还是继续生活在清朝时代的中国文人世界之中,悠游自在。我的祖母名叫曾嫦娥,更是始终活在清朝时代里,她并没受过教育,看来应该是不识字的,直到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多年了,她过的日子仍跟年轻时代一模一样:抽鸦片,到戏院看“大戏”(歌仔戏),穿着清代的闽南式衣服,头上依旧绑着镶块绿玉的黑头巾。祖父在44岁那一年的端午节(后来也是诗人节)当天,到十八尖山去作诗,回来吃过一颗大粽子,即因脑动脉破裂,随即过世。当时父亲才三四岁,我自然是从没见过祖父的。祖母则活到50多岁,晚年眼睛因白内障而致失明。她整天坐在大床上,常常要我过去摸摸抱抱,口中总叫着我这个长孙“金孙”。祖母过世时,我8岁左右,已经有足够的记忆,至少可以从她的身上拼凑出祖父母那一代台湾人活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一些零碎图像。 我的父亲叶国瑛生于年,那时日本占领台湾已有28年了,他从小就是接受日本的“领地”教育。他和祖父这一代台湾人一样,都横跨两个历史时期,也都是在20岁上下逢遇“改朝换代”的变局。可以理解的是,祖父母这一代的台湾人对于大陆可能还有着浓厚的原乡认同,到了父母亲这一代,已经逐渐丧失了了解原乡的现实机会与兴趣,更难以形塑如祖父母辈身上常见的较固着的认同意识。父亲当年从新竹到台北就读台北私立高中(即今天的泰北中学),完成高中教育。之后,曾经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所属的专修班学习音乐,停留时间应当很短暂,回台后进了新竹“州政府”工作。由于年幼丧父,父亲自小即由祖母带大,家里环境相对富裕,加上父亲又是长子,受到溺爱自是可以理解。虽非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但是受宠的父亲却有着富家子弟常见的那种经不起挫折的个性弱点。尤其是他继承了祖父作为诗人的艺术家浪漫气质,情感丰富而脆弱,一旦面对现实生活压力的挑战,立刻就显得无法承担和应对。说来,这是他一辈子过得相当辛苦,命运坎坷而乖戾的关键所在。父亲热衷政治,相较之下,我的母亲曾彩雪则相当传统,她自认是妇道人家,不必,也无法了解外面大社会的事情,她活在家庭之中,家庭就是她生命的一切。母亲也是成长于丰裕的地主家庭,18岁嫁给了父亲,本来以为可以过着少奶奶的好日子,没想到父亲“不长进”,后来得让她为全家的生计操心。母亲19岁就生下我,年农历六月十四日过世,人生只过了34年而已。我记得,那天正好是我考高中的放榜日。当我知道考取了,也正是她弥留时,我在她耳旁轻声跟她说考上新竹中学了,她点头表示知道,这一幕历历在目,我永远忘不了,尤其是她大大咽了最后一口气的光景,更是难以从脑海中磨灭掉。 年,我在新竹市的北门街出生,老家是一座当时台湾都会区常见的长条形住宅,一共有四进,几乎横跨北门街与世界街交界的整个地段,这栋有着双店面的房子是我曾祖父盖的。我出生时已经是二战末期,美军不时有发动机群轰炸台湾,新竹市正好是日本空军的轰炸机基地,因此遭到美军惨烈轰击。为了躲避空袭,日本当局要求人民疏散,我们举家疏散到新竹市郊宝山的佃农家中。 在父亲做生意失败之前,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丰裕而无忧无虑的情况下过的。我从小就是吃好穿好,又是长子兼长孙,在家备受长辈疼爱。从二战后期到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初期的一大段经济萧条时期,很多台湾人在生活上所经历的困顿,我都未曾经历过。大约在我小学二三年级时,父亲的生意垮了,开始变卖家产,把田地、其他房子甚至连我们自己所住房子第一进有店面的部分也卖了,一夕之间,家道中落,我家从大户人家变成徒有遮风避雨之住所的近贫家庭。 蔡禾:父亲的职业潜移默化影响了我 我土生土长在湖北武汉,但父亲的祖籍是江苏镇江,母亲的祖籍是安徽合肥。我父母都是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父亲学的法律,母亲学的物理。父亲是50年代初进入中南政法学院任教的,该校年与中南财经学院合并为湖北大学。年湖北大学被撤销,年又复办并改名为中南财经大学,之后又与中南政法大学合并为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可能是因为出身问题,父亲没有从事法律教学,而是教授西方哲学,为此他在年前后还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进修过一段时间。“文革”前他是讲师,“文革”后先后为副教授、教授。母亲毕业后进入中原大学(年武汉解放后南下的革命大学)集训,也正因为这一段经历,她这个从未从事过革命活动的人成了离休干部。一直到年,母亲都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做过一段时间记者,主要从事技术工作。 年湖北大学被撤销,父亲下放到湖北京山的农村(不是干校)。一般每个村子会安排几家老师落户,由于我母亲在工作单位也面临下放农村的安排,经过她申请,批准随父亲一起在湖北京山安家落户,住在一户农民家的一间土砖房里。年撤销湖北大学被作为林彪集团的错误得到改正,年父母迁回武汉,回到改名为中南财经大学的原湖北大学,母亲也就改行做了老师,讲授基建预算和计算机,先后定职为讲师、副教授。 我们家一直居住在大学校园的家属区。家属区的房子是管理干部、教师、工人混居的,不过还是教师为多,所以从小我就感受到学校大院的环境与文化。那个时候,校园里有一些年以前就是知名教授的高级知识分子,可能受到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他们见到人总是毕恭毕敬的,非常谦虚,并且不太和其他人有过多的交流,显得有些神秘,这使我们这些孩子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崇拜感。自己家里不时也会有父亲的同事来谈工作和闲聊,虽然那时候还小,父辈们所谈论的话题并不太懂,但仍然能使自己对一些词汇、话题、观点和争论变得熟悉和敏感,这或许对我后来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教职工子弟到彼此家里串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你可以在不同人家里看到不同的藏书。记得我居住的那栋平房里,有一位老师家就有全套《红旗飘飘》,我经常到他们家借阅。校园里教职工子弟之间的互动对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其潜在影响一点不亚于家人的影响,至今我还有几位从幼儿园就开始为伴的挚友,虽然他们都只是初中毕业就已辍学,但都成为77级、78级大学生,并走上了教学和研究岗位。 李培林:“文革”中父母下放,我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我年出生在山东济南,除小学一年级在青岛外,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都在济南。籍贯是山东莱阳,那是我父亲的出生地。 我父亲最早是搞小学教育的,后来考到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学心理学。但是他没有进入学界,从辅仁毕业回去以后干两年就参加共产党闹革命了,后来在胶东区党委工作。那时候有个“胶东公学”,是山东的小“抗大”,培养了很多后来南下的山东干部,他在那里当过校长。 年以后他进城,“文革”以前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工作队时期又派到山东师范大学(当时是山东师范学院),后来就留下来当校长了。“文革”后,教育系统最先受到冲击,他很快就被打倒,戴“高帽”、挂“牌子”游街。我母亲是山东总工会领导,也被打倒,不过稍微好些,没那么狠。刚开始整的是“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很快就扩展到“黑七类”“黑九类”,把“走资派”也算进去。我也成了“黑帮子弟”,在大院里玩,都是“黑帮”孩子一块玩,很孤立,受歧视,还屡被欺负,有些过去都很熟悉的人,当时面目全改。那时读鲁迅的作品,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我那时对这种世态炎凉,感受颇深。 边燕杰:父亲的文艺属性影响了我 我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工人家庭,一直到中学毕业都生活在天津。我的父母是初中文化程度,有三个孩子——姐姐、我、妹妹,年龄均相隔两年。童年时,父母的兴趣爱好带给我们兄弟姐妹很深刻的影响。父亲常年订阅《人民日报》和《天津晚报》,年轻时还是天津铁路系统工人羽毛球代表队的双打队员;母亲喜欢读中外文学作品,“文革”前家里曾有少量藏书,年轻时曾是天津市工人业余话剧团的女主演。天津是中国曲艺之乡,父母都是曲艺爱好者,周末经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剧场看戏,听大鼓书,看相声和杂技表演。受父母影响,我们三个孩子都曾是中小学文艺宣传队的演员。我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作品。 我的父亲是车工,技术级别在“文革”前被定为七级,在八级工资制时代属于工人群体中的高工资群体;加上母亲的工作收入,小的时候我的家庭生活条件很好,除了日常开支,还有文化娱乐消费的能力。父亲在年以前给私营企业当过学徒,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只身投奔东北解放区,在齐齐哈尔工作了一年多,年1月天津解放后才回到家乡,经师傅介绍到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原名“津浦大厂”)工作,一直到退休。从“文革”开始到改革开放,父亲时常怀念以前的国营工厂,说那个时期岗位管理严格,计件工资制行之有效;他多次参加铁路系统内外的技术大比武,由于成绩出色,计件产出和质量超标,技术级别迅速达到了七级。父亲由此被提干,任车间计划员,月初和月底经常在家里熬夜,拿个算盘“噼里啪啦”地核对数据。年秋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回到了工人岗位。“文革”时期我才知道,我的爷爷以前是小业主,我的伯父曾是国民党宪兵,这些家庭背景使得父亲不能通过政审,入党无缘,为此他坚定地放弃了干部职位。幸好他回到了工人岗位,不然“文革”时很可能被当作“保皇派”而横遭批斗陪绑或被抄家。我的爷爷和伯父的历史背景,对我本人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都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 注:内容仅做学术分享之用,若涉及侵权等行为,请先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