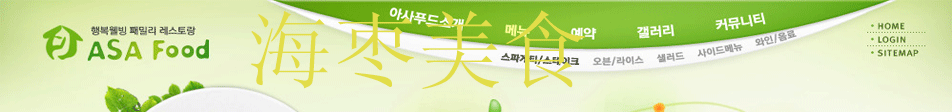|
莱阳旧店村轶事 文/赵爱萍莱阳县志點注记载了这么一段文字——清:慈霑上人观阳里人,或曰旧店,俗姓李。事母至孝,喜谈空门静理。江南讲师一生来县说法,慈霑与语相契。母没,同妻海澄祝发师之。不期年,即登座讲诸大小法乘。及一生南还,海澄止莲池庵(庵在旧店),慈霑遂入崂山,建华严庵居焉。潜心经典,老而弥笃。于诸品经多所论述。生平未尝有忌言瞋语,年八十四卒。 慈沾莱阳旧店人。生于明万历十六年(年),于康熙十一年(年)去世。关于慈沾旧店坊间至今流传着他的一些轶事。 南庙和北庙 明朝崇祯年间,旧店村有一户姓李的人家。主人自幼丧父,性情温和,待人有礼。孝敬老母远近乡邻皆知。此人聪慧,饱读经书,喜欢谈论佛门四大皆空清净之事。世间的事好像冥冥有定数。他青年娶妻生有两子,家景顺和。可天有不测风云,两个儿子年满成人求取功名时,又突遭瘟疫,不幸双双殒命。(有说旧店进士茔埋有他的两个儿子)幼年丧父,中年丧子,他万念俱灰。若不是年迈的老母还在,这人世间几乎没有什么再让他留恋的了。不久他邂逅了来莱阳弘法的江南一生和尚(临济派的第三代传人),二人交谈颇为投缘,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命运的多舛,这时他就有了皈依佛门的念头。其母去世后,一切都尘埃落定。他和妻子商议,决意出家了却凡间尘事,一心皈依佛门。随后由一生和尚为其祝发并收为门徒,取法号“慈沾(后即为临济派第四代传人)。他跟着一生和尚潜心学习佛法,深得佛教之精髓。一年后,便登坛宣讲大乘教、小乘教等诸多佛教教义。后来一生和尚离开莱阳返回南方,慈沾对佛法的修炼日臻成熟,声名远扬,拥有了众多信徒。许多向佛之人慕名而来,纳为慈沾的弟子。为了潜心修行,慈沾变卖了祖上积攒下来的殷厚家业,在旧店村建了南庙、北庙,和众人捐资又修了一座桥。他的妻子也皈依佛门,取法号“海澄”,居于南庙,名为“莲池庵”。解放前最后一代尼姑还在此庙修行,并且坊间还流传了这么一个故事:四十年代初,莱阳适逢灾年,一对夫妇逃荒途径旧店,因饥饿所致,哺乳的妇女奶水不足,怀中的婴儿,面黄肌瘦,奄奄一息。无奈之下,这对夫妇将女婴忍痛托付给庙中的老尼姑。老尼姑慈悲为怀,抱着女婴走街串巷,为其寻找哺乳的妇女讨奶吃。因此这个女婴长大以后,喊五六个妇女为干妈。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年八月初一,老尼姑八十一岁过世,女婴已长成十六岁的大姑娘了。老尼姑在世的前几年,有一个从关外回来无依无靠的贫穷青年,由村中人搭线让他居住在庙中,帮年事已高的老尼姑打理田地里的营生,意欲老尼姑过世之后,让他和姑娘结合在一起,都有个着落。后来,他们生儿育女,生活美满。六十年代,南庙被拆掉,翻新成了新房。这个女婴,现已是儿孙满堂,且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 慈沾居于北庙,北庙取为何名,已无从考证。据说这源于慈沾在旧店修行期间,半路舍庙出走。人去庙空,无人续佛,庙中荒芜一片,香火凋落。岁月的尘埃湮灭了晨钟暮鼓,它的名字也一起湮灭在尘埃里,历史的长河偶尔翻动一下,也如一缕轻烟。五十年代在北庙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其又扩建成了学校:青砖黑瓦,院内五间教室,还有一过洞,大门台,高门槛,门两边各有一石鼓。门前是石条铺成的五层台阶。台阶西侧,立一石碑,正面刻有“乐善桥碑”(慈沾捐资在南庙和北庙之间建的一座南北走向的桥)几个字,背面刻有捐资修桥人的名册及数额。因年代久远的缘故,当时这些字迹就已模糊难辨了。八十年代后期,学校全部拆除,北庙也不复存在了。慈沾既然捐舍了家业,建了两座庙,一座桥,为何又舍弃了这些,离开了旧店呢?这也是事出有因。据说慈沾和海澄虽然仅有一座桥之隔修行,但是两人自出家后,已割断了俗间情分。并商定:如有急难事,可鸣钟,击磬告知,不再相见。一年冬天,北风呼号,漫天飞雪,天地一片白茫茫。海澄正在庙中诵经,忽听庙后一声惊叫,紧接着是“啪啪”地几声响。她急忙打开后窗看,原来是慈沾正冒着雪去沟下取水。他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滚下沟坡,把水罐也给摔破了。他空手爬上沟沿,脚上的一双布鞋已烂得前后开口,挂不住脚了。早间旧店无水井,村中人吃水都是靠从村东和东南两个方向流下来的溪水汇集的一条水沟。沟两旁灌木丛生,溪水长年不断,人们只需在沟边挖一小坑,溪水渗进去,过滤一遍,然后人们用瓢或勺舀进桶内,担回家食用。再说海澄师傅看到此景,心中不由一阵心酸,她目送着慈沾走回北庙,随即取出布背、麻绳,挑灯连夜几天为慈沾做了一双针线密密的千重底鞋。她趁着傍晚人迹稀少时,将鞋放在沟边的青石板上,回庙敲响铜磬。慈沾在庙中听到磬响,出门看到青石板上的新鞋,心中也不免生情,他知道是海澄牵挂自己。庙宇相隔得这么近,难免藕断丝连,可是如此这样下去,难能修成正果。他遂用斧子将鞋剁碎,舍庙毅然离开旧店,外出云游。 慈沾与华严寺 慈沾离开旧店据说就在即墨、崂山一带进行佛教活动。有资料记载:明代崇祯末年,御史黄宗昌卸官归乡里,在即墨县城西北建起一座“准提庵”。因闻慈沾大名,于崇祯十四年(年),慈沾应邀主持“准提庵”。时慈沾年已54岁。《青岛文化》一书也有文字提及慈沾:“宋、元时期,佛教和道教两教和睦相处。万历十一年(年),明朝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和尚来到崂山,在崂山太清宫三清殿前耗巨资修建了气势恢宏的海印寺,后因与太清宫道士发生纠纷,进士出身的道人耿义兰进京告御状。万历二十八年(年),朝廷降旨毁寺复宫,憨山亦被远戍雷州。崂山佛教虽遭如此打击,但是并未一蹶不振,桂峰、自华及慈沾等著名僧人仍在崂山进行了许多佛事活动,加之有当地乡宦士绅的支持,崂山的佛教仍有所发展。据粗略统计,明、清时期建造的寺院共有20余处,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华严寺。这座寺院规模宏伟,声名远扬,藏有清朝雍正年间刊印的《大藏经》一部,还有元朝手抄本的《册府元龟》。在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华严寺与有着多年历史的石佛寺、法海寺被称为崂山佛教的三大寺院。”《青岛文化》这样记载华严寺:华严寺原名“华严庵”,亦称“华严禅院”,坐落于崂山东麓,依山面海,风景秀丽,是崂山规模最大的佛寺。属于禅宗的临济派。它是明代崇祯年间监察御史黄宗昌卸官归乡后出资筹建的,后毁于兵乱。清朝顺治九年(年)黄宗昌之子黄坦继承先父遗志施捐出资,由即墨准提庵和尚慈沾鸠工建成大殿,清朝康熙二十七年(年)增建了前楼,历经30余年全部竣工。塔院内有1座七级砖塔,系华严寺第一代主持慈沾大师的藏骨塔。禅院建成后,慈沾就以临济派第四代传人的身份出任华严禅院第一任主持。慈沾在华严寺期间,曾搭救了华严寺第二代主持善和,也就是清代农民抗清英雄于七。据传,顺治十八年(年),于七在锯齿牙山(栖霞境内)聚众起义抗清,惨遭朝廷镇压。于七逃至华严寺(时称华严庵),慈沾大师用沸水毁其面,诡称天花病僧,躲过清兵搜捕。后来于七拜慈沾为师,皈依佛门,法名善和。慈沾圆寂后,善和成了华严寺第二代主持。其又在华严寺独创了中华武术独家拳——螳螂拳,至今这套拳法仍在崂山地区流传。慈沾晚年潜心于诸家经典的研究。华严寺中收藏了许多珍贵文物,如明万历年间颁赐的描金三大佛像和许多明代版本的佛经,以及元朝手抄本《册府元龟》、憨山大师手书的中堂等均属极为珍贵的藏品,这些收藏多数是慈沾大师的功劳。他对青岛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慈沾在即墨和崂山共居住了三十年。旧店的于秀民老书记回忆,抗战时期,其父亲参加的抗日游击队曾在崂山驻防。闲暇时与庙上的老师傅谈及到慈沾。因为他从小就听村里老人讲慈沾老师傅的故事,说后来离开旧店去了崂山华严寺。庙上老师傅说确有此事,华严寺第一代主持就是莱阳来的慈沾大师。早先有莱阳来这上香拜庙的乡亲,庙上都宾客相待,管吃管住。慈沾84岁圆寂,《即墨县志》记载:“平生不为苟得,不募缘,不蓄幼童……居墨三十余年,未尝见有忌色瞋语”。 姑塔 莱阳方言中称高地为“礓”。旧店村前从东往西有一道岭,俗称“南礓”。听老人们说,以前礓西头有一座七级砖塔,塔身不大,是六边形空心塔,中间竖一根杉木杆,门窗都被砖封堵着,人不能进去。顶上层有一石刻塔帽。传说当初修塔时,塔身垒好以后,塔帽怎么也安放不好,怎么安就是不正。这时候有一个云游僧人路过,说是时辰未到,须等有人戴生铁帽子,驴骑着人时才能安上。人们不解其意,都说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呀!过了几天,正逢邻村冯格庄赶集,有一个人牵着一头快要生产的毛驴,从集上买了一口锅背着往家走。正巧这时候毛驴产下一头驴驹子,还不会迈步。天公也不作美,又下起了雨。这人急中生智,忙把锅扣在头上,抓起驴驹背在身上,赶着大驴急忙赶路。这一场景被另一个赶集人看到了,他大喊:“快来看呀!驴骑着人,人戴生铁帽子出现了!”人们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于是急忙回去招呼瓦匠们安塔帽。还真是应验了僧人说的话,这回塔帽真得就安上去了。老人们还说,有塔的时候,旧店周围一带从来没有冰雹之类的自然灾害。这也许是人们对塔寄予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吧,祈求老天风调雨顺。故这座塔有“避风塔”之称。建一座庙、修一座塔老百姓总盼望能保一方平安。村里有一老师塾先生曾为此塔写过一首诗:远望一支笔,却在水中生;风吹写文章,不知言何情。遥想几百年前的一天,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障碍眼睛的任何东西,站在高处,四望一片碧绿沃野,微风涟漪,恰如一池湖水,碧波荡漾。一塔兀立,犹似湖水中竖起一支饱蘸墨汁的笔,正欲挥毫泼墨!所以一些人又臆想把这座塔叫“笔锋塔”。“避风塔”、“笔锋塔”无论怎么命名,都与旧店人息息相关。有旧店村人听年长的老辈说,曾见过塔前有个碑,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碑已无踪迹,也无从考证。关于塔的来历,我们从健在的老人(老尼姑收养的女婴)那里得到一些真实的资料。她回忆,小时候,老尼姑师傅带着她去冯格庄赶集,在路上,曾指点给她看,说此塔是第一代师傅“海澄”的墓塔,叫“姑塔”。老师傅是坐化圆寂的。她圆寂之后,有人看到一条龙,龙尾搭在塔顶,头伸到桃源庄村东的七星河那喝水。那时,塔前不远处有一丘坟就是进士茔。一九四七年,华东野战军兵团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攻城打援,运动中歼敌”的指示,为了粉碎蒋介石摧毁胶东解放区的计划,发起了莱阳战役。驻守在莱阳的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从青岛、即墨调集了援兵,他们沿青烟北上。东线兵团十三纵队奉命在将军顶、旧店一带设防,扼烟青公路,不让敌人的企图得逞。敌人在太平庄一带设有炮兵,由于担心塔的目标太明显,不利于我军伏击,所以这座塔在当时用炸药将其炸毁。后来的人只能看到一堆碎砖烂瓦的废墟。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从倒塌的乱砖下挖出了一墓,上面盖的大理石五、六个人都抬不起来。第二天,他们用钢钎才将其撬开。墓里面也是大理石砌的,大理石上面刻有花纹。有人进墓察看,里面除了几块骸骨,别无其他。从这些迹象看,应是海澄大师的藏骨塔。海澄大师圆寂升天后,也未带世间的一丁点儿浊气,她清净地走了。据说,海澄大师的藏骨塔和慈沾大师的藏骨塔遥相呼应,在崂山可以眺望到此塔。真实也罢,臆想也罢,海澄大师和慈沾大师都应该有个美好的轮回吧。随着历史的行进,农田改造、道路整修,这些遗迹也不复存在。现在记得这座塔的人也寥寥无几了。 历史的印记 旧店囊括了莱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特点。村庄地域面积虽然不大,仅有三百多住户,但因其具有诸多优渥的生存条件,吸引了十二、三个姓氏来此聚居。该村自有开店铺的渊源,是周围商宇集中之地,故取村名也带“店”。以开店为谋生的形式,一些家族沿袭至今。像村中的于姓家族至今还沿袭着清朝之前的“永丰”老字号。二零一六年,旧店公墓内树立了一尊御旨赐葬的“龙头碑”。该墓碑出土于马山埠后于氏祖茔附近。碑体上雕有“双龙戏珠”,中间刻有“聖旨”二字。两条龙昂首扬鬣,瞪目振鳞。龙体错落盘绕居上。此碑经旧店于秀民、于春英等一些于姓人氏考察辨认,系本族五世祖之羲公的曾孙英霖于道光十二年为其所供奉的铭碑,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尊墓碑的问世,彰显了旧店村人秉承了中华民族“尊宗敬祖”、“诗礼传家”、“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 年10月20日,旧店村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开始了拆迁的工作。这个村庄即将要退出历史的舞台。翌年的二月,旧店村的街巷、房屋已参差不齐,残瓦断垣零落着。所有的事和物仿佛都沉静了下来。一棵柳树(村中人称之为“龙爪柳”)站在冷清的街道,却独领了“万条垂下绿丝绦”的风姿;它又像是一个婀娜多姿、玉立亭亭的少女,避开了尘世的喧嚣,抚弄着瀑布般的秀发,在妩媚的梳妆。 一棵老古槐虬枝缭绕,像村落氤氲的袅袅炊烟;又像漂泊的乡愁。所有站立的树,看似互不干扰,各顾各的,但是整个村庄悄悄地给它们笼罩了一层内心的拘束。 一幢老的房子前,一个年迈的老婆婆背着手,踱着步时不时的盯着门前一棵枝节错综的无花果树。这棵树金贵着呢!老人红色的帽子游移着周遭黯淡的目光,阳光都被吸引了去。像村庄还未完全消失的标志,一个打扮中性的中年妇女,在她还未拆迁的房子前,神情安然地剔除从春天的土地里挖来的一篮子荠菜的杂根和杂叶。她稀疏的头发,卷着曲发着棕红色飘曳在二月高傲的风里,既敦厚又张扬。 所有的街道和行人都显得拘谨起来。闲散替代了旧店街原来的熙攘景象。店还是要开的,东西还是要卖。趁着拆迁还未到底的空档,“永丰馒头店”当家的又娴熟的把一箱箱馒头装上了车…… 除了那些叫声有些响的鸟儿,过往这里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成了历史的声音。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