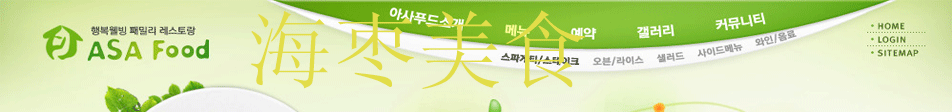|
莱阳聚焦:老家的年味儿 文/吕学超 如果,非要给过年,用一种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想,“年味儿”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它源自于我们内心,融化于我们的情感。 不知从何时起,过年不再是一种憧憬而成了一种仪式,有人说,是年味儿变淡了,大街小巷虽仍能听到鞭炮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家家户户飘出香喷喷的美食气息,但内心总不那么熨帖;也有人说,是我们长大了,价值追求和情感世界都发生了变化......而我觉得,可能是人与人之间,都读不懂彼此的世界了吧。大人们不懂孩子的世界,孩子们走不进大人的生活。的确,如果不是看到城市街头,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大街小巷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鱼肉飘香,我们真的分辨不出这是在过年,就找不出任何与往日有什么不同了。 我的家乡在莱阳农村,那时小孩子是掰着指头盼望过年的,因为他们又成长了一岁,而大人们则是惧怕过年,因为他们又年长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曾经,我一度困惑大人们为什么惧怕过年,而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对过年的记忆,也许还是停留在吃和玩上面,而吃,绝对是过年的重头戏,这也正是我喜欢“年味儿”这个词的原因。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伴随着儿歌,腊月初八,是盼年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各种豆类,杂七杂八,但不可缺少的是大枣,正如老舍笔下的《北京的春节》中写道:“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销会”。还有我们胶东独具特色的,不得不提的腊八蒜,口味独特,酸中带辣,色泽光亮如翡翠,是过年开胃必不缺少的一道菜。 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到现在,腊八的时候,多数是在学校或者工作岗位上,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悄悄地过了腊八这一天,体味不到曾经的期盼与乐趣,今年的腊八,是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爱女吕娅亭腊月初五出生,我在腊月初八那天,独自远离妻儿,重返工作岗位。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 腊月二十三,莱阳老家把辞灶日,也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有句俗语叫“灶王爷爷本姓张,一年一碗杂面汤”,每到辞灶这一天,家家户户做手擀面。儿时的印象中,爸爸是我心中的“厨神”,除了炒菜独具特色,做手擀面,也是一项绝活。手擀面宽而薄,柔而有劲道。面的口感,关键还是看卤的调制,爸爸做的卤,芸豆、葱花、大姜是必不可少的调料,经他的手一调制,估计只卖卤不卖面,也会门庭若市。辞灶最幸福的,就是能吃上爸爸亲手做的手擀面。 在莱阳农村老家,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手擀面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点半刀烧纸。焚烧完毕,将面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朝着灶台磕一个头,给灶王爷爷行个礼,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 比较讲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关东糖又称灶糖、大块糖、麻糖,是胶东古老的传统名点,即是年节食品又是祭祀用品,一年之中,只有在小年前后才有出售;关东糖是用麦芽、小米熬制而成的糖制品,它是祭灶神用的,也有人说它是用白糖加淀粉加水加淀粉酶酿熬而成,类似于麦芽糖。以前只能在过了小年之后的大集上买到,每次都会买一大包,直到牙齿慢慢变坏,蛀牙疼的厉害,才慢慢地断了“麦芽糖”的念想,现在看见麦芽糖,都经不住诱惑多看几眼,只能是饱饱眼福了。 然后再摆上酒等祭祀用品,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帝面前多说好话。正所谓农村所说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过了辞灶日,除夕就迫在眉睫了。农村就开始忙忙活活的,大扫除,蒸馒头,做豆腐,炸炸胡,包包子等,虽然忙碌,但这承载着一年的希望和祝福,老少爷们都乐此不疲。 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除夕夜翩然而至。 如果说,年夜饭太匆匆,那过年中午那顿饭,绝对堪称饕餮盛宴。在农村老家,过了中午那顿饭,一切都得为“年”服务,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人人和蔼相待。欠债的,也不能登门要债,一片祥和,幸福的氛围,而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做在一起,赏美酒,品佳肴。那时的自己可以无忧无虑地笑,肆无忌惮地谈。这是大年夜的前奏。 以前自己年纪小,一般经不起熬夜,但在除夕这天,下午必定要美美地睡上一觉,晚上是要伴随着钟声跨年的。妇女们在家包饺子,父亲和家里的长辈,则是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往往都是同宗族的男丁,成群结队,到祖先的坟头,磕头、上香、放鞭,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 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正北墙上,已经挂起了自己家祠堂的族谱,族谱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我们在古装戏里见到过的那些财主家的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族谱里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据说只有家里去世的老人,才能将名字写在上面,活着的人的名字,是不能出现在上面的,不吉利。族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香炉里插着香,这个香,就是傍晚时分到祖先坟头请回来的“香”,回家插在堂里正北的族谱前的香炉里,意味着香火不断,代代永传。讲究的人家还做几到菜,放上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还要放上几个盘,盘中放着鸡鸭鱼肉等贡品,供祖先享用。家堂族谱前的蜡烛要一直点着,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晚上不经意地看一眼,好像活了一样,冷不丁的还有点怪吓人的。 这是真正的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大人也不能训斥孩子,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要说吉利的话,比如打破碗碟要说“岁岁平安”,碰到粪便要说“时来运转”“走时运”之类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这一点还是比较讲究的。 不得不提的是包饺子,这是全国各地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我们家包的饺子却别具一格。 准备诸多1毛硬币,一般是按照人头算的,比如家里是6个人,一般准备12个或者18个硬币,将其洗的干干净净的,在开水里蒸煮几分钟,充分杀菌消毒,将硬币包在饺子里,谁在除夕晚上吃到带硬币的饺子,预示着来年挣大钱。以前自己傻乎乎的,除夕晚上什么菜也不吃,硬生生地往肚子里塞饺子,为了就是多吃出几个硬币来。晚上拜年的时候,长辈们见了小孩,总是下意识的问吃了几个硬币。自己在吃出硬币来之后,总是爱得意的炫耀一番,拿着这个硬币,在全家人面前比划比划,让全家人都知道我吃出钱来了,并且这是我自己吃的,以前爸妈为了哄我高兴,将他们吃出来的钱,放在我的饭碗底下,有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多了几个硬币。记得好几次,为了吃出钱来,连吃了3大碗,都不见一个钱子,结果撑得消化不良,差点要了小命。人家除夕晚上在家看春晚,我在撑着难受,在大街上溜达消化食。母亲担心我吃坏肠胃,安慰我说:“明天早上吃的也算”,我似信非信,直到吃的再也塞不下去了为止。饺子里还可以包板栗,预示着来年好好过日子;还可以包大枣、糖块等,预示着来年生活甜甜蜜蜜......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如果愿意,也可以将每个饺子里面包满硬币,天天吃饺子,个个饺子能吃出钱来,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 做年夜饭,下饺子,点鞭炮,一片欢声笑语。 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碗,碗里盛上两个带汤的水饺,往院子里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竿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院子中央的空地上放下碗,点燃了烧纸后,浇上刚出锅的饺子汤,就跪下向正南方磕头,以示祭拜天地。随即到灶台旁,同样的过程祭拜灶王;到正北方,祭拜祖先。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庆典了。全家人继续中午的阵势,座位原封不动,基本上也不炒什么新菜,只不过,晚上的重头戏是吃水饺。在吃完饺子之后,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一边磕头一边喊着: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这孩子真好!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以前是五块、十块,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得想雀跃了。如果你磕头的时候不喊,那可能就要吃亏了。记得我小的时候,来到一个长辈家里拜年,大人们都在寒暄,客套地说着一年来的收获,我在那闲着没事干,又插不上话,心想:反正早晚都得磕头,索性早早磕了吧,早磕早收红包。谁曾想,家里乱哄哄的一群人,自己又是小不点,要是不透过大人们的腿缝中,那是绝对看不到我的。头也磕完了,见没有人反应,担心自己刚才磕的头白磕了,就一直跪在那里,直到有长辈喊:“你看这孩子在下面磕头了”,自己这才乖乖的起身,手里接过压岁钱,紧紧地拽在手心里,手一刻也不离开衣兜。 最开心的,莫过于此。 过了除夕晚上,春节的脚步如火箭般的速度往前跑。 要说大人们真正的放松,是从大年初一开始。按照惯例,除夕晚上是给自己本族的人拜年。而初一早上,是处于五服之内的同宗族人之间相互拜年问候,当然也有例外。五服,在我们当地表示家族宗亲世代,即所谓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身五代。凡是血缘关系在这五代之内的都是亲戚,即同出一个高祖的人都是亲戚。从高祖到自己是五代,就成为五服。五服之后,则称谓“出五服”,就没有了亲缘关系,就可以通婚。一般情况下,家里有婚丧嫁娶之事,都是五服之内的人参加。 大年初一的上午,志同道合的艺人自发组织,由许许多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曲艺和文艺人才,组建起秧歌文艺队,也不乏会欣赏到老民间艺人的独门绝活,吹啦弹跳,说学逗唱。值得一提的,是胶东大秧歌。胶东大秧歌流传的面较广,如莱阳、文登、海阳等地的秧歌都属于一个类型。并都以《跑四川》小调为基础,形成了三句一加锣鼓比较定型的民间歌舞形式。每年的初一上午,都会听到广场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用鼓声唤来本村所有爱好秧歌和爱好热闹的人,同时也为许多青年男女搭建了认识和交流的平台,它的作用,一点不亚于现在的青年联谊会。 老人们拿着马扎,聚在一起,边欣赏曲目表演,边哄着孩子,含饴弄孙,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在表演的同时,时不时地还会蹦出几个特殊的“小演员”,他们虽然不知道台上在演的什么,但是,他们就是想跟台上的人一样,上去扭几圈,赢取众人的掌声和欢笑声。 对于年轻的商人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聚在广场上,聊一聊这一年来彼此发展的状况,了解一下彼此的人脉和社交,有时,也会提供不少商机。对于曾经不谙世事的我,找几个一年见一回,一回等一年的同学,喝喝茶,聊聊学业,谈谈发展愿景和希望,憧憬一下美好的未来,内心是无比的富足。 从初二到正月初十之前,一般是走亲访友的最佳时节。以前都能从初二走亲戚,一直走到初十。一家亲戚走一天,甚至感情好的或者喝醉了没办法回家的,一家亲戚也能待上几天。现在都图省事,嫌麻烦,一天走好几家亲戚,慢慢的,走亲戚的味儿也淡了。 慢慢地,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元宵节。我最大的兴趣,莫过于在元宵节当天晚上燃放炮竹和“滴滴筋”(谐音),个头大一些的鞭炮我是绝然不敢碰的,似乎大人也不让我碰,也就燃放个小的,一挂鞭都打不翻一个塑料瓶子那样的,个头和爆炸力都很弱,但足够让我痴迷地期盼一整年。记得小时候,把小的鞭炮装在兜里,左手去兜里掏鞭,右手拿着燃着的香,左手拿鞭,右手小心翼翼地拿着香,刚一触碰上燃绳,还没听到“呲呲”的声音,就赶紧扔到了离自己好几米远的地方。结果有一次拿反了,将右手的香放在了左边的裤兜里,结果,左兜里的小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了,打的我的小腿像有无数蚂蚁在腿上爬似的,自己的左腿冒起了一股青烟,吓得我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直到鞭炮响完了好一阵,我才发出恐惧的哭声,自那以后,许久不再放鞭。 一眨眼,这段故事,已经过了三十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知不觉间,岁月的沧桑已无情地雕刻在眼角,爬满了整个面庞,三十年的日子如箭穿梭。有时想想,生活不总是岁月静好,有时候赐予我们一地鸡毛,正在老去的我们,似乎一切都可以从容面对,记忆力在减退却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变的,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回忆。有些东西,像是过去的年味儿,再不记下来,就真忘了。 也正因为这些,才会不断唤起自己一直坚守却怎么也摸不到方向的初心,正所谓心随路转,越走越宽。壮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我们要严肃对待生命中的一切,毕竟这些都是单向车程,来不及回味就到站了,回过头去看过去的风景,越来越模糊。唯有不肯虚度年华,不白白地浪费时间,这样,我们的人生终会有收获。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